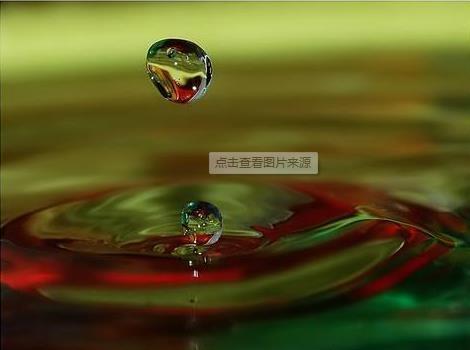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教材中所选用的《一滴眼泪换一滴水》,节选自雨果长篇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第六卷第四章,课题沿用了陈敬容译本的章节标题。笔者觉得这个译法颇不合适。其理由如下:
首先,这种译法颠倒了主客体关系。
相貌的丑陋使伽西莫多成了人们凌辱、鄙弃的对象,当他在烈日下遭受酷刑时,人们对他仍极尽谩骂、羞辱之能事;长期的蒙羞受辱也使得伽西莫多的心冷酷起来,他也用人们对他的凶恶的态度来憎恨别人,以至于当前一天晚上遭他劫持的爱斯美拉达走上了刑台时,伽西莫多坚定地认为她是来报复他的,愤怒而轻视地想把刑台打个粉碎。至此,雨果将伽西莫多人性的被蒙蔽渲染到了极致,为下文人性的复苏蓄足了势。
当爱斯美拉达以德报怨“迅速地走上了刑台”,“从胸前取出一只葫芦,温柔地举到”他干裂的嘴边时,美丽与善良如一道天国的光辉瞬时照亮了他混沌的心灵,唤醒了他长期被压抑的人性,融化了他那颗日渐冰冷的心。这个从未受过人间温暖的畸形儿第一次流下了感激与忏悔的眼泪。
从上述情节来看,爱斯美拉达的一滴水是伽西莫多一滴眼泪的前提,如果译为“一滴眼泪‘换’一滴水”则颠倒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。
其次,这种译法不能体现出原文的艺术力量。
雨果说:“取一个形体上丑怪的最可厌、最可怕、最彻底的人物,把它安置在最突出的地位上,在社会组织的最底层、最被人轻蔑的一级上,然后给他一颗灵魂,并且在这灵魂中赋予最纯净的一种感情,这种高尚的感情根据不同情况而炽热化,使这卑下的造物在你面前变换了形状,渺小变成伟大,畸形变成美好。”(《雨果论文学》第104页)渺小、畸形的伽西莫多之所以能人性复归,变得伟大而美好,正是爱斯美拉达这一滴善良的水的感召。也就是说,正是这一滴水,换来了伽西莫多的眼泪。这一滴眼泪标志着伽西莫多从此摆脱了宗教愚昧的束缚,恢复了高尚仁慈的心灵,步入了善良人性的正道。或者说,伽西莫多的眼泪是为这一滴水而流,是对这一滴水的报答。此后,他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少女的感激和爱,从绞架下救出爱斯美拉达,并最终用正义结束了邪恶的克洛德的生命。可是如果照课题译法,这一滴眼泪就成了换来一滴水的前提和代价,眼泪与水之间就成了买卖双方的契约,爱斯美拉达的以德报怨、真诚善良和伽西莫多的人性的复苏就都荡然无存了,小说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在标题中也就无从体现了。
那么,此处究竟该如何翻译呢?目前书市上的译本不下二十种,除了陈敬容的译法外大致还有三种译法:一是管震湖、智莉、陈宗宝、潘丽珍、朱颐等人的译本,这类译本译为“一滴水,一滴泪”。二是孙娟等人的译本,该译本译为“一滴水,由一滴眼泪回报”。三是李玉民、施康强、安少康等人的译本,此类译本则译为“一滴眼泪‘报’一滴水”。根据上文分析,笔者认为李玉民等人的译法比较契合原文的表达。
各种版本的差距如此之大,原因何在?笔者又查阅了法文版和英文版原文。法文版原文如下:une larme pour une gout te d’eau(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),英文版原文如下:a tear for a drop of water(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)。以英文版为例,由于for一词的多义性,此句的表达颇为复杂,既可以译为“一滴眼泪‘换’一滴水”,也可以译为“一滴水,一滴泪”,又由于“for”的本义是“为了”,也可以译为“一滴眼泪‘报’一滴水”。法文版与英文版类似,pour一词也具有多义性。由此看来,各种译本之间存在差异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翻译工作很不容易,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更高。傅雷说:“任何艺术品都有一部分含蓄的东西,在文学上叫做言有尽而意无穷,西方人所谓的between lines(弦外之音)。”“翻译应像临画一样,所求的不在形似,而在神似。”好的译文要传神达意,要表达出原文中最深刻、最具神韵的东西,是必须对原文作深入的理解和研究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翻译便不仅仅是文字的转换了。